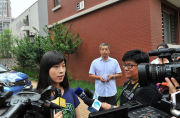本篇文章1765字,读完约4分钟
江剑鸣(平武) [/s2/]
我小时候,赵文金们家前面的房子后面有七八棵梨树。 当时优良的矮化品种不流行,梨树都是五层楼那么大的树。 岁月的风霜,在黑黄色的树皮上,像沧桑老人的额头一样,酝酿着许多纵向的皱纹。 树干要两个人才能抱起来。 几年后,他们家整修房子,砍倒梨树做柱头,木匠说这是附近修房子中最大的柱头。

他们的庭院被称为方法堂水库,高村乡街以南有广阔的田水库的正中央。 每年春天,有几棵梨花盛开,碧绿的小麦和逐渐开放的金黄色油菜花田水库里,耸立着或落下几棵雪白,在麦苗上,在油菜花上,介于绿色和白色之间,在黄白之间。 梨花飞舞,暗香四散,麦苗和油菜花的清香,漂浮在法堂水库的田野之间。 很遗憾,那个时候谁在悠闲地欣赏呢?

那几棵梨树有几个品种。 火燕梨、青皮子、麻粒、芝麻点、算盘果。 火燕梨和青皮子的水果都是青青的。 咕嘟咕嘟、芝麻、算盘的果实都呈麻黄色。 算盘的果实最小,成熟期最晚,大部分麦苗出土后,打几个霜才能吃。 那个梨虽然砂粗、水分少、口感硬,但是煮了之后会很好吃。 我很喜欢青皮子,汤碗大,水分足,口感软甜。

一个地方的果树是最代表家乡味道,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东西,不管是酸还是苦。 你知道悉尼、鸭梨、香梨、苹果梨这个品名是几年后的事了?
哪棵梨树自己长得高,按季开花,结果,成熟,不需要像杨家的桃一样防止别人来偷。 事实上,那棵树的高度,连主人的房子都很难采摘。 水果成熟后,树自然落下,只能由人们捡起来吃。 其实,那个时代摘了也不敢上街卖。 其实,大部分水果都烂在树上。 只有喜欢吃梨的黄蜂,才会嗡嗡前后忙,在树上尽情地吃。

看到树的果实成熟,蓝皮果,泛着黄光,田堤散发着梨子的甜蜜气味。 诱惑啊,不仅仅是孩子。 生产队的年轻人趁着工作喘口气的时候,摘一点,大家一起尝尝新鲜感吧。 赵老爷搬来了两台梯子,唐文友等几个年轻人,把两台梯子链接在一起,挂在树干上。 赵老爷再给他们一次竹竿,竹竿的一端编着小笼子。 爬树的人把小竹篮伸向梨,剜了一下,梨就掉在笼子里了。 回收篮子,拿出梨,用布口袋卸货。 摘下的梨,大家随便吃。 梨多,不需要像孔融让那样让。 有几棵梨树,连着两个梯子也够不到树丫,年轻人已经只能徒手爬了。 真惊险啊! 当然,这些时候,我和赵文金都在树下,眼花缭乱地等待着。 如果没有手臂,即使他是树的主人,也没有先享受的权利。

几年过去了,在我能爬树自己摘梨之前,我一直被黄蜂折磨着。 那时,我终于爬上了。 赵文金等兄妹在树下看着,摘着梨等着顺路。 旁边有嗡嗡的黄蜂声,我不这么认为。 突然,头被刺伤了,吓了一跳。 我一只手抱着树枝,一只手拍了拍头顶。 啊,又被捅了。 我急忙退到树下,几乎一边翻滚一边爬上树来,头上扎了三支箭。 不能吃梨,赶紧跑去公社医院。 吃梨之类的黄蜂,毒性好像不太高。 医生给我头上抹了点食盐,一天后就消肿了。 几年后,我的熟人真的被蜜蜂蜇死了。 据说那是四叶草,毒性很大。 被黄蜂叮了,昏迷不醒,也有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情况。 据说现在的蜂子由于化学药品的驯化而提高了毒性。 不知道这个真假。

高村乡街两个生产队,400多人,除了街南法堂水库赵家有梨树外,街北前两队周家只有梨树。 那棵树再大,再高,连最会爬树的唐文友也不太容易爬。 周家是水冬瓜梨,钵很大,一个有一斤重,一次吃不完一个。 梨不能和别人分着吃。 把梨分开,用谐音分开,说不吉利。 人们总是在语言方面寄托着美好的愿望,总是希望人们永远不离开。 但是,擦河的人喜欢吃梨,不知道谐音是否分开。 姚叔叔说,离孩子远点也不吉利。 说是吃梨,谐音很麻烦。 我们工人很辛苦,所以使劲吃饭。 道路修好后,山外来了人,记得买他家的水冬瓜梨吃。 也有人爬树剪树枝,回嫁接。

不知道周家的梨树还在不在。 1969年修路,赵家翻修房子,梨树全部被砍作房屋材料。 道路整修后,乡街上游三里路的水桶坝这个生产队,种了很多新品种的梨树。 1975年,我离开磨刀石川的时候,看到水桶坝的员工背着大大的背上的悉尼前往公社的收购站。 哪个背上的梨,汤碗大的,青皮上飘着黄色的亮度,散发着浓郁的香味的甘甜。 一见到我,他们就慷慨地拿了几个,给我吃。

几十年后,在杯子有意义的餐桌上,吃了很多颜色鲜艳的季节水果,但没有当时磨川的果树的甜味。
谭鹏
标题:【快讯】江剑鸣:永不分“梨”
地址:http://www.mahamoni.com.cn//myjy/16297.html